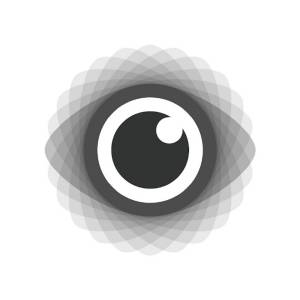南唐画家顾闳中作为皇帝李煜的「眼线」,去往大臣韩熙载家中,将自己观察到的觥筹交错画成了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一千多年后,艺术家王庆松请来栗宪庭扮演当代「韩熙载」,召集了一众打扮艳俗的女子。他自己也躲在每个画面的角落里,模仿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拍摄了《老栗夜宴图》。
将场景放大至一个时代,王庆松同样扮演着顾闳中那样的观察者和记录者,他像作品中一样无处不在,却又好像始终游离在画面之外。
初见王庆松时,我们边吃饭边闲聊,有人问了句:“老师最近在关注什么作品?”答:“「三十而已」。”他当时穿着最普通的宽松 T 恤和休闲裤,带了好几包烟,大多是贵不过 20 块的金桥,云烟,黄鹤楼;点菜时,只要求一道土豆丝。
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独特的发型,即使看过王庆松作品的人,大概也很难在人群中认出他来。更不会把媒体笔下那些「中国最贵摄影师」「观念摄影领头人」的标签跟这个中年男人联系在一起。
「乡愁」就是,想起那个地方会去看看吧
2015 年,在纽约生活的第三个月,王庆松感觉自己无法忍受下去了。他也试图学习过几次英语,都没什么成效,这次决定彻底放弃。如果再来美国,就还是让妻子代为翻译。不过在这个环境继续生活下去,恐怕妻子会太辛苦。
在 2003 年拍摄《跟我学》时,他大概也没想到那满黑板的英语单词,会让十几年后的自己发愁。
语言,生活习惯,节奏,当然都是问题。他之前约一位美国朋友吃饭,对方不接电话,转去了语音信箱。这一点也令他烦躁,为什么美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好好接电话呢?为什么吃顿饭要提前一周约定呢?
他曾在英国遇到一个从小被领养的华裔,祖籍应该是四川,但从没在中国生活过。那个人告诉王庆松自己爱吃辣,喜欢太极。这让王庆松更确信,有些东西就是在骨子里,改变不了。比如作品,“怎么可能脱离中国这个环境呢,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,这就是我的东西。”他说。
一切都是「拿来」和「送往」,没有任何问题。
但更小范围内关于「乡愁」的东西,他不太确定。1969 年,刚刚 3 岁的王庆松就和在油田工作的父母从大庆搬去湖北,到了江汉油田所在的潜江。在那之前,一家人因为父亲转业,才刚刚从祖籍地江苏迁到大庆没两年。
身边都是和他一样的外来孩子,他从来没学会过那里的方言。“没有理由学啊,那边没有亲戚,只有父母。”他说。语言习惯并没有带来生活上的不便,只是好像,会让他无法与那片土地产生更紧密的联系。
来到北京二十多年,他一开始连水都喝不惯,现在讲话仍能听出些南方口音。可回想起湖北、潜江、沙市,除了一些食物偶尔带来的熟悉味道,23 年的经历好像也不能在王庆松心里拼凑出一个「故乡」的样子。
江苏和大庆就更不用提,那时他甚至还没生出成熟的记忆。“我的「乡愁」可能就是,想到一个地方,会想回去看看吧。”他说。
不惹事,也不怕事
作品中只要出现了王庆松的面孔,除了一头似有似无的乱发会给人留下印象,人们对他使用最多的形容词就是「黝黑」「黑得发亮」。
那种肤色与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的户外工作者有点区别,又不像刻意美黑的人看上去健康。他的身材体态也不如多数同龄男性那样明显发福。二者结合,会让人觉得他「精神不错」,「年轻时可能吃过苦」,但也「不太好惹」。
王庆松在江汉油田当过七年油田工人。1983 年高中毕业,他作为第一批进入钻井队工作的「油田子弟」,和被他称为「地方老百姓」的当地老乡分在一起。“那时候哪里有油,队伍就搬去哪里,”他说,“拉着铁皮房,像游牧民族一样,永远没有固定的居所。”
那段日子的回忆大概也像他的作品一样,被褪去了些饱和度。工作的辛苦暂且不提,「地方老百姓」第一次碰上子弟,总是觉得王庆松好欺负,三番两次挑衅。
钻井队的活有时候没日没夜,大家累了躺地上就睡。一天早上,王庆松接到提醒他上岗的电话,起来准备去工作,发现很多人都看着他笑。他在脸上抹了一把,手上都是黑黑的铅油。
“谁弄的?”他问大家。得到答案后,他抄起管钳冲向那人,想也没想就挥了下去。「扑通」一声,那人倒在地上好久才爬起来。
“怎么弄都有个底线吧,你不要给我搞一些很过分的事,总要嘲笑我,这时间一长就是忍受不了的。”王庆松如今回忆起来,觉得那群人是没事找事,自己属于沉默后的爆发,想想还是很解气。
还有一次,他和朋友吃过早餐,有人拎着刚出锅的油条贴着他身后经过。隔着白背心,王庆松被烫得够呛,他当时只说了句:“你注意点啊。”那人没吭声,坐到一边去了。
但朋友却一直咋呼“你这白背心废了!全是油!”说得多了,王庆松心烦意乱,火一下子窜上来。
“谁弄的?”还是那句话。隔壁桌一个人站了起来。王庆松上去先是给那人嘴上一拳,又穿着油田劳保鞋一脚踹在了他肚子上。周围的人都蒙了,没一个人敢动,就那样目送王庆松离开。
肋骨被踹断了三根,当天还是大伙儿为他出狱接风的日子。被打的哥们儿记恨王庆松,拉上几个人说要砍他。
“可我从那经过了啊,他根本不敢砍。”王庆松说。
大概是「光脚不怕穿鞋的」,十年之后,那人成了当地一霸,还在打听当年打他的人是谁。不为别的,就是单纯觉得是个牛人,想认识一下。
“不惹事,不怕事吧。”王庆松说。打架这件事已经离他太遥远了,但这句话仍是真理。
我就是想看一眼
离开油田前,王庆松一个月能拿到 400 多块的工资,而普通人就几十块。那些钱也足够支持他过些不一样的生活:“八十年代的彩色电视机,3000 多块,市里只有三台,这种东西,你必须得要吧?限量的进口裤子,用的料子好,一百多块,绝对要搞一条。”
「必须」「绝对」,听起来都有些暴发户的口气。但不管他有没有钱,都爱图点新鲜玩意。
1991 年去读四川美院时已经没有工资可领,王庆松平时的娱乐活动是去跳「砂舞」。
“学校附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老礼堂,或者电影院,交一块钱进场,可以在里面一直跳。”「砂舞」几乎是那个年代和地区最流行的娱乐活动,一个舞厅里可能有几百个人,男男女女身体紧贴,跟着歌曲扭动。歌曲选的都是舞曲片段,中间关灯的环节,大家会开始动手动脚,过一会儿,灯光又突然出现。
还有些区域,灯光昏暗,或者一直都是黑着的,偶尔有亮光扫过,可能会出现点奇怪的画面。
王庆松当时在群艺馆学过国标,但站在那中间还是有点起鸡皮疙瘩,不如同去的朋友如鱼得水。除了偶尔跳舞,他去「砂舞」更像是现在的网红打卡,看看不同的新店门票有没有涨价,在卖什么新饮料,去跳舞的女孩又是哪种类型。
大多数「砂舞」场所如今都被取缔了,偶尔还能找到那么几家。有时候去成都,他会去看一眼。“但一进去,发现我挺老的了,别人都是小孩,我都不太好意思看他们。”
他也去过老年人的「砂舞」场所,自己又变成里面最年轻的一个。跳舞的女人他估摸着至少都有 40 岁以上,有的只穿着内衣。
“原来想过要不要拍一个这种东西,后来觉得拍不了了。你说它可能也不是色情,但里面确实会有些交易。”王庆松说。
他本人对肢体亲密接触是有些反感的。曾经有个关系不错的法国朋友,见到王庆松就激动地大喊:你太帅了!(王庆松说:怎么可能)接着会扑上来,逮到脑袋哪里都亲。“恨不得就亲嘴了。”王庆松说,“我不喜欢,受不了。”
但在各式的发廊、澡堂、按摩店……这些总是透着些暧昧和艳俗的场所,他又都有过不同的体验:纽约的同性按摩店,他觉得是他感受最好的一次,会推荐给妻子。韩国 KTV 里的小姐,他敬而远之,又非常好奇朋友说她们的胸部都是假体是否属实。
“可以接受的事,我都想去看一眼。”他说。
现场小记:
采访当天,王庆松直言自己前一天痛风还吃了海鲜,有些不适。坐在沙发上休息的间隙,他说这都是小问题,自己之前得过禽流感,高烧到 40 度,差点没挺过去;还有戊肝,医生问他是不是去了非洲,或者吃了垃圾,怎么能感染这么罕见的病。
他大概是将这些被动接受的痛苦也看作人生的难得体验,讲述时竟有点「活着就是赚到」的兴奋感。可以接受的事,对他来说太多了,他完全没有大众对艺术家刻板印象中的「不接地气」,会从任何微小的角落里获取信息。他的助理抱怨跟他一起看「乐队的夏天」会失去很多乐趣,因为他总是能以自己的理解,从某个并不高高在上的视角去评价每一支乐队,且一针见血。
能够看破,偶尔说破,王庆松仍能真诚面对观察到的一切细枝末节。也许这些碎片只会成为他「压缩饼干」般的摄影作品中不被人注意的小点,但对他而言,来过,看过,感受过,就真的是在人生中「赚到了」吧。
文_yini|图_王庆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