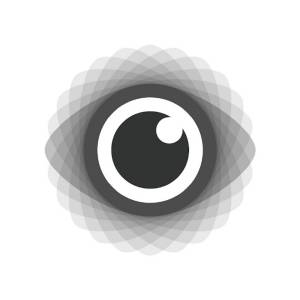你上一次买杂志是什么时候?
学生时期,大家只要路过报刊亭就会停留一下,看看有没有最新的杂志,冲着封面是自己喜欢的明星,零花钱是可以不花在吃上面的。但,互联网爆炸兴起后,纸媒就持续势微。而今年的一场疫情更是让很多杂志停刊。包括 《Playboy》、《朝日相机》这种时代载体。
今天的 Finder 就聊聊两本今年停刊的大刊,《PAPER》、《Q》。
被骂出名的《PAPER》
《PAPER》今年的春季刊,邀请了 Lady Gaga。配合着她新专辑里的「仿生学」概念,用到仿生动物、机器人、时装、AI 元素,非常时尚的未来科技感。而在这之后的一个月,未来不来,ENTtech 的 CEO 兼创始人 Tom Florio 宣告,《PAPER》杂志停刊,并可能不再回归。
理由很简单,在纸媒势微的大环境下,又来了一场新冠疫情,生意做不下去了。他也选择了裁员,并实施高薪员工减薪 20%-30%,而他自己减薪 60%。
一代顶流大刊,就这样在互联网和疫情的双重夹击下,选择消失。
Tom Florio 并不是杂志的创始人,《PAPER》是他在 2017 年从 Hastreiter 和 Hershkovits 那里收购来的。这其实是一本创刊于 1984 年的杂志。
在这之前得另说一款周刊,《SoHo Weekly News》,从 1973 年创刊到 1982 年休刊,一直是当时纽约排名第二的周刊,被称作「可以替代报纸的报纸」。因为报道纽约市中心的新音乐艺术家们,被大众熟知。
Hastreiter 和 Hershkovits 都是那里的前员工。一个是时尚编辑,一个是新闻编辑。
1982 年春,美国陷入了经济衰退的困境,整个社会环境都非常糟糕,大家都不敢任性地创造新鲜事。但他们俩不是。总有没钱的玩法,他们创办了《PAPER》,最开始就只是一本 16 页的黑白月刊,报道着和时尚、音乐、艺术有关的讯息,还有各种夜生活。
到了 21 世纪后,杂志慢慢调整成了季刊和数字化,也尝试过出版《20 Years of Style: The World According to Paper》、《From AbFab to Zen: Paper's Guide to Pop Culture》这类解读流行文化的书籍。但一直都小众得不温不火。
直到 2009 年,Katy Perry 和 Mariah Carey 登上封面,杂志转型成功。章子怡和张曼玉也前后登上封面,而且在那时就可以慢慢看出《PAPER》的风格化,会挑选名人的另一面。
但真正让杂志出圈还是靠卡戴珊的全裸。
法国摄影师、画家、电影制片人和设计师,让·保罗·古德(Jean-Paul Goude),堪称创作多面手,被称为「image maker」。他在 2014 年为金·卡戴珊(Kim Kardashian)拍了一组全裸写真,刊登在了那年《PAPER》冬季刊上。
封面上写着「Break the Internet」,打破互联网。一场来自纸媒直接的宣战,为达到目的,同样用了粗暴的裸露手段。
互联网确实一下炸开了锅,但基本上都是骂声、吐槽声,大家都在说《PAPER》为了流量没下限、低俗炒作、传播错误价值观、鼓励整容...同行也会指责《PAPER》恶意营销。还有付出实际行动来凑热闹的,他们开始 cos 卡戴珊,以此嘲讽。
但这种黑营销放在现在而言,大家见怪不怪了。娱乐至死的背后都是一群「死就死吧」的人。比如,大家一边骂着,一边将这一期的线上杂志浏览量冲到了最高,《PAPER》官网在那一周里的流量,比前三年的总和还要多。
尝到甜头后,《PAPER》找到了一种博关注的发力方向,骂声就等于流量。所以风格化在那之后,越做越有。每一次的出刊,都在制造话题。大胆前卫的拍摄风格和顶级的流量,让《PAPER》开始被各种名人追捧。
Rihanna 变成杀马特、Katy Perry 漂白眉毛、Paris Hilton 黑化、Miley Cyrus 全裸玩猪...每一个放现在都是一个热搜。明星热衷于这种不同面貌的曝光,且关照着多元群体和态度表达。
这种顶流大刊宣布停刊,其实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是种「突发行为」。2017 年,Tom Florio 收购了《PAPER》,那时就已经将主营业方向往互联网整体迁移,毕竟在全年的数据中,《PAPER》网页浏览量同比涨幅在 400%。
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,除了电子版的封面之外,《PAPER》还和 YouTube 合作推出了 PAPERVIEW 视频栏目,最近也打造了播客 Internetty。整体战线就基本转向线上了。所以遭受疫情冲击后,他们优先的就是放弃实体书。
“虽然可惜,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”,Tom Florio 说。
是谁杀死了《Q》?
2020 年 7 月 21 日,《每日电讯报》刊登了一篇文章,《The death of Q magazine is a symptom of an expert-free internet age》,《Q》杂志的消失是无专家的互联网时代症状。
从前几年开始,这本英国最具权威性的音乐杂志就已经开始进入瓶颈期,而新冠疫情让这个瓶口收到了极致。7 月,编辑 Ted Kessler 在推特宣布,7 月 28 日出刊的《Q》就是这个杂志的最后一期。
3 月,英国开始大范围防疫封锁的时候,各种音乐杂志行业的人就预感到了后续:各种酒吧、livehouse 关闭,相应就会出现更多线上免费资源。没有人做新专辑,没有音乐节,大家都宅在家中。没有新鲜事。
而作为音乐杂志里的扛把子,《Q》其实在 21 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2001 年的 20 万本就是销售巅峰,之后迅速降到每月平均销量大概 2 万 8 千本。很显然,还是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。而这次疫情让这个老牌杂志,彻底崩垮。
Ted Kessler 在宣告停刊的推特里说到,“在我任职其间,其实公司已水深火热,我们一直想尽办法令杂志在印刷出版业中苟存一口气,但疫情令我们的努力化烟。”
最后一本《 Q 》是特别收藏版,里面收录了不同年代的采访,包括了 David Bowie 、 Joni Mitchell 和 Prince...随便一篇稿子就是一个时代,毕竟这是一个有着 34 年历史的传奇杂志。
1986 年 10 月, Mark Ellen 和 David Hepworth 创办了《Q》。最开始是打算叫做「cue」的,取其「播放音乐」的意思,但又怕重名,直接用一个字母来替代了。从创办开始,这本杂志就一直关注着摇滚、流行和各类小众音乐。从 1990 年开始,每年还会在伦敦举行颁奖晚会,是国际音乐领域的风向标。
创办初期,整个社会都被朋克洗脑,大家都在追求躁动、反叛。而《Q》在那时逆向而行,第一期封面人物就是 Paul McCartney,它在试图让那个急冲冲的社会停下来看看那些更早年代的人。之后,还推出了 Rod Stewart、Paul Simon、Elton John、Genesis、Eric Clapton...
从那时候开始,这个红底白字的大写 Q 就和世界的音乐动态强绑定了。
往后的 10 年里,它的封面开始出现代表着英国摇滚年代的各种人物,U2、Oasis、Radiohead、Madonna、Prince、Kate Bush、Nirvana、Britney Spears、Beyonce、Kanye West...成了各路歌手打歌的首选媒体。《Q》也开始评选各大排行榜,比如百大专辑、百大英国专辑、百大最富有摇滚明星、史上百大单曲等。就这样,一步步奠定着它的音乐权威地位。
其中有一档专栏,「Who the hell do they think they are」,作者是英国音乐记者 Tom Hibbert,言辞非常辛辣刁钻,让当时很多乐人害怕,但备受读者喜欢。
但随着互联网的瞬时兴起,明星们开始自己经营社交平台,SNS 上的话题度比权威性更加吸引人。一篇耗时半个月的采访不如明星的一条 30s 小视频。
《Q》也尝试过顺势而为,也想用更有热度的名人来撑场,但已经明显被时代抛弃了。
还没和互联网和平相处的时候,又来了一场疫情。《Q》的母公司 Bauer Media,其实在 5 月时试图将其出售,但没有吸引到合适的买家,大家对这种权威性的纸媒早就失了兴趣。就在 2 个月的挣扎以后,最终选择了停刊。
很多乐迷对此都无法接受,但都想了想觉得停刊也挺正常。这,可能就是这些纸媒人感受到的时代悲哀吧。
文_德克斯特|图_网络